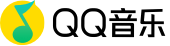简介
岜農身高腿长,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生人,在南丹读完高中,本是想学美术,考广州美院过了专业课,却因为英语失之交臂。2006年前后在广州组建“瓦依那”乐队,据说在壮语里“瓦”是花,“那”是水田,“瓦依那”就是稻花飘香的田野。 在广州的几年,岜農主要是做设计和画插画,还在光孝寺工作过,《那歌三部曲》是陆陆续续创作并完成录音的,时而回老家春耕秋收,时而自学田野录音。2012年岜農回家修建房子,在父母和当时的搭档索力的协助下一起在院子里亲手盖起了谷仓和隔壁的录音室,名之曰那田農舍。 2015年,岜農正式决定彻底回家种田,但也是在2015年,瓦依那正式发行《那歌三部曲》,包括了《飘云天空》《西部老爸》和《阿妹想做城里人》三张专辑,在创作上基本和五条人《县城记》《一些风景》同期,但最终问世后,岜農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很多在城市居住久了的人,都向往“归园田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或者辞掉工作去大理丽江,但更多的人只是暂居,或者旅居,岜農却是扎扎实实种地十年,即便是从2015年算起,也有八年光阴,偶尔在农闲的时候,经朋友介绍去演出。而在种地的时候,岜農选用的也是很科学但又很原始的自然农法。 “广州是我认识音乐和音乐人的地方,我的音乐世界是从广州打开的,我在广州看了胡德夫,看了野火乐集,看了林生祥,开了很多眼界,我承认城市是学习和做事的地方,但生活,我更喜欢回到乡下”,岜農说他写出了《阿妹想做城里人》,有很现实的考量,也包含了当时自己婚姻的苦恼。“低头种地,抬头唱歌”,看起来很浪漫,但做出决定,且坚持十年,并不容易。太多的人控制力不够,岜農说回到乡下之后谢绝不必要应酬,自己找乐子,种地种菜养鸡之外学习和制作新乐器,乐在其中。 岜農说更喜欢农村的生活,可以做想做的事情,在广州只能是个小人物,但回到故乡,可以收集童谣、整理传统民歌,当然也可以种田,并且根据自己的方式施展拳脚,“很多乡下人外出打工,为的是回乡建个有罗马柱的楼房,安装上很气派的铁门,但我更喜欢就地取材,没什么必要做很虚荣很表面的事情,我去学自然农法,利用自然的力量让土地更肥沃,让居住更舒服”。 很多人觉得瓦依那是原生态的民谣乐队,或者演唱传统民歌的乐队,这样的认识过于偏狭。岜農在思考自己和农田的关系、农业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之余,很多时间都在学习音乐,自制乐器,研究编曲,研究效果器。在音乐的路径上,岜農说自己不算幸运,歌迷的接受度不算很快,但其实瓦依那的歌包含了很多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而不是只唱花花草草。 “瓦伊那最初甚至不算一个乐队的状态,我们没有跑场,没有宣传,是我创作完了,拉几个老乡一起排练一起录音。多数时候是我创作和编曲完成了,找几个老乡来帮忙,然后他们又在外地工作,在酒吧调音或者教学,这些工作只有城市才有”,两年前,经常在街边卖唱的桂林歌手十八到那田農舍帮忙收割,后来十八在桂林做演出邀请岜農做嘉宾,再后来杭州酒球会的十周年演出,邀请瓦依那,缺一个鼓手,就叫了当时在工地打工的路民,三个人就重新组队了。 十八自称是岜農的歌迷,做流浪歌手的时候也唱过瓦依那的歌;路民早年曾在广州打工,因为弹吉他结识了现在的太太,做音乐之余,很多时候靠在工地打工赚钱养家。岜農算是七零后,十八是八零后,路民是九零后,重组后的瓦依那乐队相当于三代人,但都是广西人,十八一直不用智能手机,他说不是不用,而是和自己无关。 最年轻的路民有健康的体魄,成长经历坎坷,自己写的《阿妈归来》催人泪下;十八本来学机械,进过电信公司,做过游戏,但最喜欢的还是做流浪歌手,创作并演唱的《大梦》堪称一个人的心灵史。岜農说很欣赏这两位兄弟,都能够保持写歌去看待自己的生活,三个人一起做了“岜農大米,世界一体”瓦依那种地十周年音乐会,让岜農增强了信心,就继续走下去。 瓦依那推出《那歌三部曲》后,《河水清清好洗手》等歌曲在小范围流传,因为远离了商业行为,他们的创作和演唱保留了非常难得的质朴和纯真,做音乐的态度得到了老狼等前辈的赞许。岜農在种地之余,研究了树叶吹奏,自制了葫芦琴、巴乌和各种打击乐器,在传统乐器的基础上又针对性的发挥,还在指导十八全新的吉他弹奏方法,以及让路民练习竹筒鼓。 岜農说自己做音乐的立足点是编曲,演唱反倒不是自己的重点,因为会自己编曲,就更能找到符合自己音色的意境。十八和路民加入后,瓦依那可以有更分明的分工和和声,岜農开始研究用电吉他模拟当地乐器芦笙和葫芦琴的音色,研究电吉他的和声风格和民族器乐的结合,“电吉他包容性强,做音乐就是做没人做的才好玩嘛”,岜農说自己也根据当地山歌创作了《遥遥寄微入远方》,把传统的旋律用全新的方式演绎,让传统旋律更有活力、更有现代感。